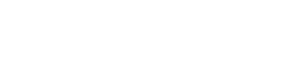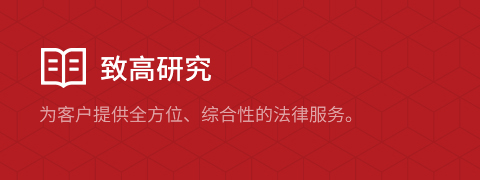一、假药罪的前世
打击药品犯罪,经历了逐步加重的立法趋势。刑事立法在一段时间内以行政管理为标准,没有重视刑法的法益保护原则与谦抑性原则,导致实践中出现问题。
此前假药罪的演化:

有严打假药犯罪的刑事政策考虑,反应在司法实践中,导致刑罚适用的泛滥。因为“行为结果”的缺失,不需要证明因果关系,为刑事入罪提供了便利条件。
当然,面对“药神”情况,司法机关并非机械司法,法律界也出现不少出罪的观点。
二、法律的“形式正义”与“实质公平”
金华的江湖郎中倪海清的“祖传秘方”成了当地一种能有效缓解癌症症状的中草药秘方,但倪海清并未对其秘方申请相应的批准文书,据很多患者的描述,使用了倪海清根据秘方生产的中药后,病情有明显好转。
2013年,倪某因生产、销售假药罪被判刑10年。
北京某药店销售11盒日本眼药水,被处以销售假药罪。常见的私自销售国外壮阳药、保健药,销售“祖传秘方”民间自制药品等等,均有被按生产销售假药判刑者。
电影《我不是药神》原型陆勇案不起诉决定书(沅检公刑不诉〔2015〕1号)。检察官在不起诉决定书中解释道“如果认定陆某某的行为构成犯罪,将背离刑事司法应有的价值观”。
陆勇在34岁那年确诊慢粒白血病,吃了两年的瑞士抗癌药格列卫,花了56.4万元。不堪重负的他改用印度仿制药,而这种药的价格只要瑞士药的二十分之一。陆勇后来将印度仿制药又推荐给了其他病友,还帮忙代购。
然而根据原《药品管理法》规定,进口药需要经过临床监测,还需拿到药品进口注册证。因此,陆勇代购的这些印度仿制药,即使在印度是合法生产,疗效也得到患者的认可,但是在国内它仍属于假药之列。后来陆勇在看守所里待了135天。
1002名深深感激陆勇的癌症患者曾在联名信上签字为他声援,检方决定对陆勇不予起诉。
陆勇案,没有进口批文的“假药”与真药疗效一样,价格相差20倍,陆勇的行为被人认为是义举,但法律上被认定为假药,刑法上被认定为犯罪。
陆勇的行为违反了当时《药品管理法》规定,在个人生命健康与国家的管理性规定相冲突的情况下,本应当优先保护人的生命健康。
刑法上对假药的界定应该依照药品的自然属性,即是否具有治疗功能来认定,而不是根据行政管理的需要来认定。
对不符合药品管理制度而生产、销售、进口的药品,不足以对人体造成损害甚至是有疗效的,是否应当按照生产、销售假药罪论处。
修订后的《药品管理法》与刑法修正案11顺应了这样的呼声。
三、功利主义刑法对行政法的僭越
《我不是药神》有句台词:“救人的行为,你管他是违不违法。”影片中办案民警也提到,“如果办理这个案子,病人买不起进口药,又没有疗效一样的‘假药’,就是在断人活路,病人只能等死。”
2011年之后,刑修11之前,我国生产、销售假药罪的立法,企图通过刑事打击,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,刑罚色彩浓重,致使刑法对行政法的僭越。
此前相当多的药品犯罪案件中,司法机关依据行为与行政法意义上的假药来确定刑法的适用,而不探究是否导致人体伤亡,即便是在说理部分对伤亡结果有所提及,甚至试图对假药进行刑法独立评价,却只是基于量刑的考虑,但最终仍不影响犯罪的成立。
141条的生产销售假药犯罪侵犯的是混合法益,一是人身健康,一是管理秩序。人身健康是自然犯范畴,用危险犯来解释、打击,不会有什么问题。但管理秩序法益,在刑法之前还有行政法规制,刑法对其予以调整需要慎重、谦抑。
否则,行政法与刑法毫无区别的规制违反管理秩序的行为,刑法入罪口子太宽,处罚太严厉。犯罪行为与违法行为的区分,用之不慎则会导致刑事问题行政化或是行政问题刑事化。
当实行行为损害主要法益,危害公民健康,并且具有一定危害性时,就应当发挥刑法功能,惩罚犯罪。若是实行行为仅仅危害次要客体,除非危害性极大,否则不能成为刑法肆意的理由,应当为行政处罚预留必要空间。
假药罪中“社会危害性”直接指向药品监管秩序,但“秩序”由于其固有的抽象性,并不包含“量”的内容,难以区分危害性大小,甚至可以说违反秩序只有“是否”的问题而没有“量”上“多少”的探讨空间,因而在解释秩序时,容易泛化,一经实施便是犯罪。
四、不看广告看疗效
修订后的《药品管理法》与刑修11之后,“假药”的认定不再依赖于行政法的视角。《药品管理法》对于假药与劣药的认定,并非根据药品的致害性作出区分,而是综合药品致害性、药品专利权和药品行政管理体制来认定。
删除了“假药”、“劣药”必须依照《药品管理法》予以认定的规定,回应系列“药神案”的裁判所带来的社会公众对于法律“形式正义”与“实质公平”的迷茫。
将以往单纯行政管理意义上的假药(药监部门禁用、无证销售、骗取注册等),以是否“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”为标准划分处罚界限:作为具体危险犯予以入罪,对于“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”这一构成要件要素有证据能够证明。
对于假药的刑法打击,《药品管理法》与刑法规范的保护目的存在很大的差异。
2019年《药品管理法》规定,“药品所含成分与国家药品标准规定的成分不符的”是假药,但是如果该成分的差异完全不会影响药品疗效,也不会带来副作用,刑法或许很难将其认定为假药。
五、药品管理秩序犯罪的变化
刑修11改变了以往自然犯和法定犯一体化规定的做法,将2015年《药品管理法》“按假药论处”的进口药从刑法第141条中剔除,专门设立了第142条之一予以规制。
同时,将本罪确立为具体危险犯,以区别于刑法第141条销售假药罪这一抽象危险犯。
增设了刑法第142条之一第2款,肯定了本罪与销售假药罪与销售劣药罪的想象竞合,按照处罚较重的处理。
从黑作坊生产出来的“编造生产、检验记录的”,当同时出现药品成分与药品标准的成分不符问题,该行为就属于一行为触犯两罪,择一重罪处理。
142条之一对管理秩序的侵犯,仍可能构成非法经营罪、走私罪。
六、“足以危害人体健康”的标准
司法实践中,对“足以”的理解经历了从结果危险向行为危险过渡的过程。
《关于办理生产、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中对于“足以”有界定。根据该解释第三条的规定,经省级以上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设置或者确定的药品检验机构鉴定,生产、销售的假药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,应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的“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”:
(一)含有超标准的有毒有害物质的;
(二)不含所标明的有效成份,可能贻误诊治的;
(三)所标明的适应症或者功能主治超出规定范围,可能造成贻误诊治的;
(四)缺乏所标明的急救必需的有效成份的。
生产、销售的假药被使用后,造成轻伤、重伤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,应认定为“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”。生产、销售的假药被使用后,致人严重残疾,三人以上重伤、十人以上轻伤或者造成其他特别严重后果的,应认定为“对人体健康造成特别严重危害”。
由此可知,该解释界定“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”,还是从药品本身的特性出发。